我會好好的 音樂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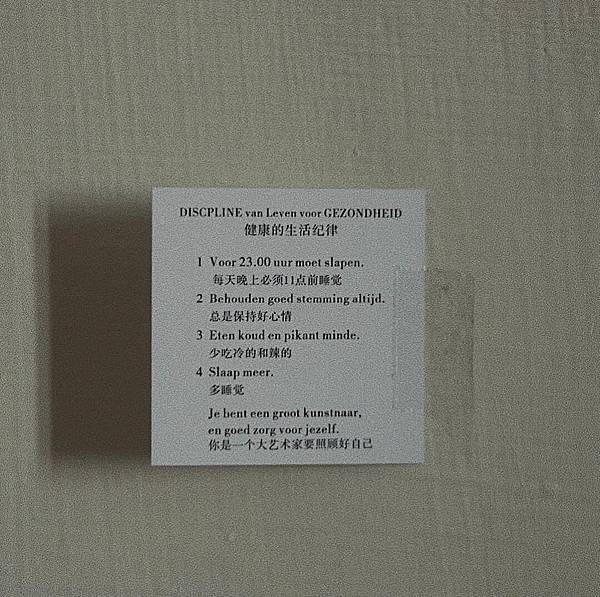
「你是誰?」
我是一個故事主角,也可以說是註解;代表一段人生的起承轉合,再各種旁白邊上註釋。
那扇門緩緩推開,散落的漫畫、打斷的藤條,及一個傷痕累累的瘦小身軀。
這次的故事由這開頭,色調逐漸泛黃。
該用怎樣的形容詞來描繪已經無法精準定義,世人都知道與“我”無關的事再精彩也只是想賺人熱淚。
這次打算平鋪直述任其發展,說不定峰迴路轉,亦或是無人回應。
即使如此,即使如此?即使如此。
門開啟後的世界隨著物轉星移,一連串的風景颯篇而過,藉由回憶牽動。
再這按圖索驥是無法找到心中所想的,只能靠情緒潰堤後去盡力描述。
而悲傷的過剩進駐使得留給其他出口的路都被堵塞,僅留一點虛偽的縫僅供社交。
「接下來要去哪?」
我也不知道,只能說對於“準備”我沒有太多的預設。
「所以你真的打算離開了嗎?」應該吧,我非常非常非常需要一個出口供我再次逃避。
有預設立場,就會期待。
有期待,就會想辦法具現化。
而無法實現的期待,最終會變成一種病反噬生而為人的根基。
「可是你不是應該已經走得差不多了嗎?」所以呢?
人生的道路在哪裡?生而為人該如何是好?
悲哀的是,身處於怎樣的位置就會有不對等的道路,怎樣才算走完?是期盼還是期待?
時間推延至人生第三段布幕,門後色調依舊。
過於凌亂的房間,散落的雜物、未整理的衣物,以及斷了一條弦的吉他。
他說他心中再無火花,剩下的路都像在等死。
想問他什麼時候開始的,他搖了搖頭,只關心如何安然的結束。
「他就在那容光煥發地唱著,眼鏡之下依舊是那對頑皮的神情。」
創造歷史的人,終究避免不了被歷史淹沒。
記錄了一生,什麼也留不住的往下一個“一生”繼續輪迴;快樂與悲傷交替而過,時而暫留時而飛逝,任憑烏雲之上的神靈肆意玩弄。
「再一首?」心裡的聲音這樣告訴自己,愣神一回的同時像是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望了眼鏡子。
想當初先出發再說時,也是為了什麼,心裡哽住了什麼,打算寫個一首歌來完成自己。
而一首再一首,一段再一段,一杯再一杯,什麼都流下了,卻也什麼也沒留下。
說不定其實不適合做這件事,不適合誇大海口成就那遙不可及,生來就不是那麼的幸運,何必強迫自己逆天改命呢。
「曾經的你不是這樣的啊,那時的你有光有熱,很多人因為你而成為了更好的自己了呢。」祂義無反顧地反駁著我,可能是知道我們來自同一個聲音,有一方的消逝也伴隨著另一方的陪葬。
再無數的遺憾中製造快樂,而這樣的快樂轉瞬即逝凝聚成更濃的悲傷,我覺得我已經無法再這樣下去了。
「所以你富有同情心,幽默感;以及容易看穿人心的能力。」玉米這樣結論,眼前的浪翻起雲湧。
但我永遠無法理解該如何是好。
故事該如何開始?
我想,先從那次跳海講起好了。
-荒腔,走板-
青春是場大雨,唷不對,那是九把刀說的。
要我說的話青春就是一本故意寫錯的劇本,不應該存在於人生的初章。
所有的遺憾、錯過、陰影都在這腳本一一奉上,我能做的就是無可奈何的演。
然後領取一份名為“教訓”的報酬。
而底下的掌聲七零八落。
明明是七個人的聚會,但到場的卻只剩六人。
忘記了是什麼原因,主揪居然沒有蒞臨現場。
「那這個包就叫做小A囉。」我大方地拿出破爛的後揹包給大家標記打卡,每一個有團體照的地方都少不了“她”的陪伴,像是真的如影隨形般地參與了我們的這場聚會。
「來!一二三!YA!!」小宇前一秒還好端端的拍照,下一秒就被丟進了海裡,連同單眼相機。
而我們七個人不過就是一齊經歷了一個盛夏的喧囂,再暑期尾端用填充適當的快樂去欲蓋彌彰之後不告而別。
最看重這段聯繫的是小A,所以小A發起了幾次的相約,可能多多少少人數上以及名單會有更改,但我知道每次都是先問我。
而很久很久以後的我才知道為什麼我會擺在先被問的這個位置。
六個人用雙腳遊歷了府城的各個名勝,適合人走的或者吃的我們都恰巧的用當時的青春去揮灑。
到了俗稱黃金海岸的海邊時,不約而同地把每個人都丟進了海裡,包括“小A”。
我永遠忘不了小A電話那頭過分誇張的大笑,以及聲音尾韻那一點若有似無的咽。
「你覺得小A再難過嗎?」小宇是和她同一組的小隊輔,時常看到他們同進同出的,像極了愛情萌芽時。
「我怎麼會知道呢?」我靜靜端詳濕搭搭的“小A”,大概回去要先曬個一兩個禮拜才能揹吧。
就在那個暑假過後,我們回歸了各自的學校及早規劃好的繁忙,彼此連結似乎也只剩下社交軟體上的留言哈哈,這個夏天像是一個例行的暑假作業默默地繳交了一篇青春過去。
只有她。
「明天去府城找你好不好?小Ta。」此時的小A在島的另一頭敲著鍵盤這樣說。
「怎麼這麼突然?」而我對這突如其來的邀約感到困惑,但心裡還是挺高興的。
「你們上次聚會的時候我沒跟到啊,想說剛好你也在府城,你要陪我走過你們走的路。」小A。
「好吧。」我謹慎的敲下這一字一句,接著懷揣著忐忑簡單的打掃了一下房間。
說是要來玩,應該沒想過要睡飯店什麼的吧。罕見地把床鋪拉出來清掃了一翻,順便把棉被枕頭都丟進洗衣機洗。
「想到唷?」隔壁房的室友坐在客廳沙發上看電視,看著我往返房間陽台奔波不解的說著。
「偶爾也要乾淨一下吧。」我衝衝忙忙的噴上幾下廁所芳香劑,試圖壓制累積已久的男人汗臭。
隔天我騎著不適合載人的檔車去府城車站等候小A。
其實也才用一個暑假認識了她,同樣有著經歷過半夜被孩童尿醒的惡夢,在荒蕪人煙的曬衣場肩靠肩用力戳洗著浸溼的內衣褲。以極其歪七扭八的姿勢頭靠頭昏睡於擁擠的巴士行李暫放區,這些寶貴的資糧都成為她在高中三年結束後最華麗的謝幕。
「喂!」突然一愣神,有個聲音拉我回來。
「我那邊叫你這麼久你都沒聽見唷!」小A出現在我右後方,輕輕地拍著我的腦門。
映入眼簾的不同於暑假慌亂時永遠洗不乾淨的隊服,她穿了一套符合這年紀女孩子會有的青澀,無袖的淡黃內飾配上蓋不上肚的薄外套,再搭了一件似乎是當代女孩子衣櫃裡都有的小牛仔短褲。
「我以為妳會從那出現。」我手指了指該是月台出口的方向,錯誤的等待習慣讓我猛然想起小A是從南向而上的,該是反方向。
「那既然我千里迢迢來了,你打算載我去哪裡玩呢?」小A揹著像是停留的三天兩夜的背包環顧了一回車站的人潮。
該去哪?來到美食之都我想應該沒有什麼比吃撐更重要了。
所以這段時間我們把可以吃的地方都騎了個遍,燒烤、火鍋、夜市牛排、牛肉湯、鍋燒麵,甚至連這輩子從未去過的酒吧我們也去點了兩杯調酒湊湊熱鬧。
她大把大把地笑著,拍了拍我說些剛上大學時有趣的事;眼神裡是害羞,也是撫媚。
合租的國宅我躡手躡腳的把小A拉進房間,記得是某個連假,屋子裡除了不想回家的我以外只剩下一個為了生活再上大夜班打工的同學。
可能是酒精的作祟下,洗完澡的小A順走了一件我衣櫃裡的一件球衣連頭髮也不打算吹的躺臥在我床鋪上,昏昏沈沈的要我為她按摩。
她說她走了一天累死了,我下意識的把燈轉至小夜模式。
「我們是朋友吧?」
這句話發生在按摩時,小A拉著我靠近她胸前說的。
「我們是朋友。」
而我再吻和下一個吻之間回覆她,一切像是順其自然、水到渠成。
「朋友會這樣嗎?」
她別過臉避開我視線這樣問,而手卻不自覺得抱的我更緊。
褪下球衣,眼前還能遮掩的只剩純潔無瑕的白色內褲,我順勢的把它也脫了,讓劇情脫稿。
「朋友不會這樣。」
接下來可能是因為我們都不知道大夜班的同學是否在隔壁房,屬於朋友間的誤會關係發生的靜謐、緩慢,伴隨些許喘息及汗珠我們時而擁抱時而掙脫就這樣折騰至快清晨時。
直到聽見房門外的外門被打開,咚咚腳步聲疲憊走過客廳及門外後開啟隔壁房門,直至重重摔落於床上。
而小A的頭髮已乾,取而代之濕潤的是雙眼及身軀。
「問你喲。」小A。
「嗯?」我。
「為什麼你浴室裡會有女生的沐浴露洗髮精?」精疲力竭的小A挽著我的手,喘著粗氣問著。
她注意到再失控前我抽著鼻子聞了聞用另一種眼神看著她,而回憶裡熟悉的味道讓所有原本不該發生的事發生在不該發生的人身上,這騙不了人。
「我不打算騙妳。」說出著句話的同時,小A摟著的手更緊了些,強行令我匍匐在她發育未成熟的胸前,似乎像是想用身體留住什麼。
該說她個子也算嬌小,只是攤上了我這“大人物”顯得更無力抗拒。
我知道再下一句話,我們這樣的關係以後連面都見不上了。
但如果不能再坦誠相交後誠實面對,愧對於這時間我們倆建立起來的社會基礎。
我們誰也說不清這關係該如何是好。
「妳跟她有點像。」但我還是能分辨她們之間其實還是存在著極大差異,甚至說唯一的共通點只有一個,誤入歧途。
而恰似這共通點,讓我習慣性的傷害了她們。
只需要一點點溫柔、一點點不負責、一點點同甘共苦的經歷,甚至是一點點有別於別人的不幸家庭背景,溫柔鄉會在夜色的掩護以及酒精的造勢下一點點的敞開。
「在你眼裡,我是個怎樣的人?」回憶裡的“她”這樣對我問,再回北向車次月台前丟下這麼一句。
「玉…」我望著“她”離去的電扶梯,齒輪一節節的搭載著新的人離開我的視線。
眼前的小A像是得到一個肯定的答案後,轉過身入眠。
事過境遷,她和小宇結了婚,生下一對雙胞胎。
-惜福,結緣-
阿輝哥,以前在單位長大時第一個交到的好兄弟。
純樸憨厚的個性體現在童年時是沒有問題,但當我們越長越大,阿輝是我們這幫兄弟初期意識到自己越來越不快樂的個案,也開始在人生任務上各個關卡處處碰壁。
一個很冷的冬天,阿輝哥離開了,也才而立之年。
群組裡充斥著RIP和不捨的貼圖,順便預約了告別式的家族邀約。
只有我默默的暗自為他喝采,終於離開了這痛苦的世界。
像是換了一個身份供別人擷取,打籃球的哥們也開始不特地再班級群組上Tag我。
身旁的人取而代之的是一首又一首的民謠,把流行歌編成組曲、吉他社團課時坐在新入社學妹旁摸她的手、處心積慮誇獎唱的不怎麼樣但身材不錯的女同學當主唱組雙人團體。
生活逐漸被音符佔據,而歲月和熱量也替換了另一個模樣世面。
少了陽光下揮灑的汗水,我習慣性動不動就往冷氣房塞,逮到機會碰到吉他一定千篇一律的唱上那幾首口袋歌曲。模樣是深情、歌聲是動人,撇除專業也算是才華洋溢。
「管家,我晚上想聽你去唱歌。」對話發生再好幾年後我做海邊的小小民宿管家時,而她是個沒有旅行目的的旅人。
H,溫州來的鋼琴老師。
像是把一切都交給了旅行的意義,只是這次栽在我這。
「可以啊。」當時的我習慣獨自一人看淡人生,自以為是傷痕累累的躲在靠海也靠山的木屋安分當個現實社會的局外人。
而這段人生的我也開始習慣身上沒幾分盤纏,無時無刻想的是蹭免費的飯及酒。
敲了敲對面另一間民宿夥伴的門,借了頂給工人防災用的安全帽,我載著H騎往了夜晚駐唱的酒吧體會人生。
這幾天H很喜歡注意我去哪晃晃,當我牽著狗時她會幫我帶上看了一半的書,晃了晃車鑰駛她就自發性地關了房間的所有燈。
幽謐的山谷她拉著我裝腔作勢的害怕,月牙的海灣我倆躺在同一片石路上頭靠頭講心事,她說她這趟旅行沒有目的是因為當時我問了她一句。
「離開這後,去哪?」
「我也不知道。」H拖著碩大的行李搖搖擺擺的走近房門前,像是用盡力氣後淡淡的說出。「好像都可以。」
「沒什麼想法的話就暫住在這吧,每天幫我打掃屋子,抵房費。」我說著這句話的同時,私心其實是希望她拒絕的,但是她答應了,原因我也是後來才知道。
可能真的不同於她所經歷的吧,我注意到她在台下看過來的眼神是如此迷戀,像是陶醉或是逃離。
任由音樂和酒精流淌,我唱了什麼及她喝了什麼完全都不重要,只知道今晚是她待在台灣的最後一晚,明天過後這一頁就將翻過去不復重來。
當晚我們面向海產生了許多對話就各自回房安睡去了。
直至隔日薄熙散去,H帶著行李箱再離開咖啡吧前對著我說。
「管家,不用送我到車站了。」當時我沒聽懂,或者說;聽懂了,沒去做。
再回海邊民宿打掃時我注意到她留的信件,顯眼的擺在了我習慣拿吉他位置的桌前。
『私心的希望你一定要記得我。』
反覆的讀誦,回憶湧現;無論是牽著狗隨意海邊漫步,騎著車迎著風雨唱歌,抑或是那幾句對白。
我想,我稱職的當了一個管家,協助銜接了旅人與旅程之間的間隙。
而這樣的過程恰巧是我決定逃離了現實社會後的天職,像是酒精存在的意義於依附慣性脫離日常偽裝,讓每個人再一個陌生人面前可以放肆大笑大哭,讓腦海裡拓印上一段失序,以至於往後再面對失衡時不會顯得格格不入。
他們也以某個形式烙在我生活、念想,偶爾午夜夢醒失眠時就提取一點攤平審視,脫口而出某些話語時發現某幾辭語被擅改,這些突如其來的發現總能讓我眼前世界再次模糊,只顧徜徉。
只可惜再當下我總是無話可說,直到當下變成過去,此刻病成躁鬱;我開始理解了“她”。
「我第一眼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這樣的人了。」這句話發生在我們認識了八年後,不變的依然是兩瓶酒、一片海。
「你在我面前不用那麼逞強」
「也不用在勉強自己」
「反正我知道你」
「所以你想笑就笑想哭就哭」
「人生已經很難了,沒有必要再委屈自己」
「你已經活得夠辛苦,把自己埋得夠深了不是嗎」
「可以了」
玉米坐在靠海的候車亭上揮了揮逼近的蚊子,她又再次在我需要某種依靠時出現;不得不感嘆命運是真的會被牽引的,只是往往我們以為需要時其實是時機未到。
時序不被合理推進,劇情前後章節出現了各自的矛盾;在年輕時選擇了老成,又在長大些時越活越幼稚。
這之間的戲謔成分只有玉米看得出來,兀自把自身攪進摻和。
「諾,叫我放下的人,還不是自己逃來了。」玉米看著我笑了笑,畫面熟悉的相似。
「我想這也是符合我人設的舉動吧。」我握著廉價酒瓶一股腦兒的灌,仰頭抬起的視線剛好望向被寄託的月,無論是牽過的手還是倚著肩都不復存在。
玉米不阻攔,配合著我也把酒瓶揚起,注意到她眼角有濕,不需多言語、無聲勝有聲。
有些關係不知道怎麼開始,但它會自然而然發生;也不知道怎麼結束,卻往往會戛然而止。
玉米總在我以為就像是每個被翻篇的一頁皺摺時,舊舊的出現在我新的篇章。無論我是哪種身份哪種名字她都見識過,並且參與其中。
這樣幸運且獨一無二的存在我私心希望如同對話般賴著,即使待在令她難受的城市生活後。
「我知道你沒辦法答應我,但我還是一樣會再你需要我時打著燈籠來找你。」玉米淚流滿面地對我說。而我明明知道玉米其實才是最需要陪伴,最需要有人能夠給她力量。
「妳,好多了嗎?」問這句話的同時,心裡隱隱作痛;但故事還在繼續,生活還在延續,我必須要讓劇情順理成章下去。
「你說呢?」玉米突然拉過我的手,玩弄掌心上的細紋,順著右手刀側描了一條弧直至食指中指間隔前,像是畫了個欲言又止的笑臉。
而這一切的開始都怪我。
記得第一次單獨和玉米看過的海,從台中南下的列車我們在充滿美食的都市相遇。
可能因為我們很熟了,沒地方住的玉米自然而然在我租屋處下塌。
「誒,怎麼你這邊都沒有給女生洗的沐浴乳啦!」玉米指著一罐三用的洗澡乳嫌棄的說。
「阿我們就四個男生住,請問是要用多好?」我連忙拿起那罐我賴以為生的洗澡乳,以一個貼臉大拇指比讚來作為話題終結。
「我不管,你去買。」玉米也不管衣服已經脫到一半只剩浴巾包裹,徑直走向客廳電視機前耍賴。
「別啊,現在很晚了耶。」我望著氣噗噗的玉米,深怕我的其他三個室友此時推門而入,那我就真的要跳進黃河了。
「你不買,我就坐在這沙發上不起來,你同學回來時我就拉開浴巾給他們看。」玉米的倔是我早已耳濡目染,為了怕造成誤會我趕緊踩上我的單車搖搖晃晃地去全聯搶關門時間。
而再我買回來後,玉米可能也是擔心我室友之後的“另眼看待”,也不廢話直接去盥洗。
百無聊賴地玩起了當時正夯的「Tetris Battle」,與各國的玩家盡情廝殺。看著眼前各種T轉高手轉的我暈頭轉向的,我聽到浴室門打開的聲音。
「怎麼會有人買這個。」玉米指著那罐寫著“花王”的洗髮精說著,而順著洗髮精的底部有個女人的照片映入,應該就算是給女生洗的吧。
「反正還是香香的啦。」再玉米走來正要拍我時,鼻尖湊去她未乾的頭皮聞了聞,而這動作也不小心撞到她的頭。
「白痴。」玉米自顧自的從我碩小的衣櫃中翻出一件...球衣,反覆聞了聞後直接套上。「這就當我今天的睡衣啦。」
「隨便妳。」我關上了燈,突然想起玉米似乎是怕黑的,順勢把燈轉成小夜模式,就自己躺上床去睡了;而玉米似乎奔波了一天也累了,習慣性的伸出手拉著我睡去。
直到我現在閉上眼時,依舊能看見電腦上的方塊,心思停留在那個房間,久久不能散去。
-奔跑,跌倒-
約定好失去的倒數時刻,心中的坦然和忐忑是相互撕咬的。
我們正和以往的誓言背離,直到重新界定了將來不再打擾的默契。
被愛著的人聽著,恭喜你和愛人有了不對等的課題。
你要早睡早起多多休息,他要用盡生命愛你。
恭喜你被愛著,也希望你一直以來都能如此;別再讓那個愛你的人獨自面對黎明。
搭著台東往台北的列車,隨手在手機裡面買了一本電子書「解構愛情」。
但是看了幾頁後笑了一下。
「原來我已經到了需要看書才能了解愛情的年紀了。」看了幾頁後索性不看了,看窗外風景吧。
和小沐相約在台北火車站中午的時刻,但還沒九點就到目的車站了。
那天是我們相約來分手的,而原因也只是千篇一律的她劈腿了。
站在黑白相間的台北車站大廳等著小沐,有一個外國人打趣的問說我怎麼站在和別人不一樣的地
板上。說著說著打開手機給我看,有關台北車站#Hash Tag的人們都是坐在黑色地板的。
而我突⺎站在與眾不同的白,倏忽間不曉得自己身在何處。
我猜他只是想搭個話,在這個陌生的國度。
懷揣著期盼想要做著跟這個人文空間符合的事情時,突然出現了我,折射了建立好的價值觀,他的眼神想是想要確認些什麼。
我用簡單的英文能力告訴他,我不曉得這個地方有這些潛規則打發了他。
小沐出現時,那位外國人還在黑白各處和不一樣的亞洲臉孔聊天,像是這樣可以搜尋到自己在這異
國的象限一般。
看著小沐看像我的神情,再次確認我的象限,像是我們困難的跨越兩條相交的線來到一個生澀的角落,右上角是她們,左下角是我。
「所以妳們再一起了嗎?」即使今天約會結束前我們還算是有一段關係的,但我還是想問。
可能這就是嘗試著置死地而後生吧,雖然我只是單純想死。
「我又不一定會跟她再一起,我只是被她瘋狂吸引罷了。」小沐別過臉,拉著我的手匆匆地走在台北City。
我也不打算戳破她,人生中積攢的失去也不少了,我開始有點習慣當下這種消逝。
漫步時望著牽著的每雙手都是正在感情的進行式,可能前晚在床上時臉和臉還貼著說過永遠愛你,可能傳著一封又一封甜膩的訊息預約了今天的風和日麗,也有可能不小心貪了一杯把愛說得太快造成了誤會。
可能也只有我們是再替感情做告別式,為將來的不再聯繫做足準備。
一路上小沐逮著機會就跟我說在學校裡和“她”有關的趣事,無意識再各種場合不約而同的說漏嘴。「我不想聽。」我揮了揮牽著的手拒絕對話。
「你不是都會想聽我在學校發生的嗎?」小沐一臉無辜的問,自始至終她都是少了筋的女人。
「但是這段回憶有了那個女的我就覺得不太舒服。」早在前幾個禮拜,和小沐的日常對話時她就說過,班上有個女生特別的要好。
「勳,我今天早上被欺負了,室友拉我肩帶啦,但我有拉回去所以扯平了。」
「勳,室友說如果我沒有男朋友一定會把我掰彎,怎麼辦?」
「雖然我是個雙性戀,但我會一直愛你的,廷勳。」
就在幾次打鬧過後似乎那個室友就產生了對小沐的興趣,而我知道此事時只是完全地相信小沐;現在想想至於該相信什麼似乎也都無從考證了,只覺得可笑。
沒想到小沐是那該死的雙性戀,沒想到近水樓台先得月,沒想到小沐會以這種方式讓我成長。
像每個被渣男渣女傷害過的劇本一樣,不甘心和自我懷疑一時間湧上心頭;為了不破壞心中還有愛的形象,費盡心思裝乖。
「再三個月。」
「多了一個我。」
「你要更乖。」
「我想帶給你很多幸福。」
這段互相擁有的日子我文思泉湧,覺得未來充滿希望,寫了幾首勵志的歌,可見愛一個人真的會有力量對抗世界,改變自己。
然而。
「以後不要再傳感人的話給我了。」
「李宜珍不想看到。」
「我一想到你就好內疚。」
「真的希望你過得很好。」
畫面、對話、記憶、願景,就都停留在那個時空;而我的一部分也就在那時死去,軀殼裡的所有只想等待燃燒後灰飛煙滅。
此時心中再無火花,對人的相處鍍上一層灰;而玉米剛好出現在台北的某處黑白相間。
「我懂你,我完全懂你。」玉米坐在我對面這樣對我說。
而我百無聊賴的被困在丟失的街道上,和玉米有一搭沒一搭的對話著。
「我被劈腿的時候,他講了很多我也怎樣怎樣的。」玉米在談論那個讓她變成這樣的男人。「然後他就提到你。」
「我?我怎麼了。」我望著玉米似乎是委屈習慣了,但這樣的習慣嘟嘴似乎也只有對我才會顯示,真實的她。
「你不用想太多,他就是藉口說我都跟你睡在一起,也是背叛他,所以他才報復什麼的。」玉米。
「唷?!我沒想過他這樣想我呢。」我回憶起和她初戀相遇時的場景,記得我把這人設定在一個哥們的地位。
走過繁華城市的街口,玉米像是想到了什麼對我說。
「先不要講他了,我覺得這是我們認識這麼久以來,你第一次用一半以上的自己面對我。」玉米接著說。「我知道從以前到現在你都在裝,現實社會需要什麼你就裝作什麼,搞得好像你很融入大家一樣。」
「聽起來似乎是呢。」何止是,簡直完全對。
「但你從來就沒有像你所表現的那樣堅強。」玉米說這句話的同時,我看到她的淚痕。
而我察覺到有什麼東西湧上心頭或是哽住的同時,趕緊分離此刻我的情緒讓它飄渺於意識與呼吸之間;這是我賴以為生的技能,能夠保護我脫離太過於快樂或是悲傷。
她說,我看起來跟任何人都很好,但心裡都保持著距離。
人生經歷太多失去,可能過了一個雨天就是道別那天;但玉米始終都在一個後會有期的明天等待。
「我覺得妳是一個好人,也是一個過來人,到了這個時候我才能越來越懂妳再對我說這些話的同時需要對自己多殘忍才能侃侃而談。」我回應了當時在月台前的那句疑問。
而玉米早已踏上了尋找另一個“他”的車程上了。
-追生,夢死-
下一世還沒來,我倒在孟婆橋前苟延殘喘。
孟婆問「確定不先喝一口嗎?可以讓你恢復如初的。」手上搖了搖那晚清澈的湯,湯面上浮現的是我的臉。
原來這就是死亡,怎麼和活著沒什麼區別。
「你沒了目標,不再暢談未來,不算活著。」牛頭拎了一根鐵鍊,鐵鍊後綁著的是變老後的我。
我環顧了一圈地獄的景象,沒想到裝飾得挺居家的。
「錯了錯了,他還有九十九個劫還沒渡完。」閻羅王不耐煩的揮了揮手上的生死簿,黑白無常一腳把我踢回陽間繼續受苦受難。
「余敏妳說,這一切是不是真的沒道理呢。」我端著她靜靜的走在隊伍中間,玉米默不做聲的陪著我們走這一哩路。
前方是各種唱誦及肅穆,後方有哭啼和歡笑,人們魚貫而行順著潮汐的路線沿路撒花。
「沒道理的事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吧。」玉米回答著我,順勢地想捏過來但距離不夠就放棄了。
「為什麼有人善良一世,就不特別被老天爺疼愛呢,像我...」剎那間,被玉米瞪了一眼,做出了一個不許再這麼說的神情。
「話說,你沒有覺得很奇怪嗎?」玉米望著隊伍前方的金碧輝煌這樣說著。
「嗯?什麼奇怪?」
「如果你以往經驗是脆弱,別人就會離開」
「那為什麼你脆弱了那麼久了,我還沒離開。」
「我是妳的社會實驗?」
「想多了吧,我要社會實驗幹嘛?」
「或許是你第一次遇見我時就知道我沒那麼堅強。」
畫面像是回到匆匆忙忙趕上的暑期營隊教室,圍著一圈的新進小隊輔順著視線看看我,再看看手裡拿著小熊的她。
「這麼說也沒錯。不過我只是想告訴你,不是誰都無法接受你的脆弱;人本來就有堅強有脆弱,如果接受不了,表示你們不適合,或是他不值得罷了。」語畢,隊伍在一張大長桌前停下。
最前方的大磬一聲敲,身穿袈裟的老僧深深吸了一口氣,起了第一聲梵唄。
“
「管家,真的很感恩可以遇到你這麼棒的人。」H再我唱完後這樣對我說,而我注意到她桌上已經乾了三個酒瓶。
「沒有妳說的那麼好啦。」我連忙攙扶起快倒了的H,深怕她一個閃失,傷身又傷心。
「你有一種治癒的氣息,以後會常常記得你對我說過,惜福才能結緣的。」H說完這句話直接摔在我懷裡,像個孩子一樣睡著了。
而她手機裡訊息一亮我看見了手機螢幕,才知道她不是旅行沒有目的,而是來到這就找著了意義。
那是一張早上在駐唱的音樂吧對街紅綠燈,遠遠的拍下了我坐在窗邊看書的照片。
手賤的我滑了滑她手機裡的流水快訊,裡面充斥著各種家人的不諒解與遭難。
這時H突然的牽我的手,嘴裡不停喃喃自語。
「管家,我愛你。」”
一跪拜,身旁的人像是大夢初醒般意識到老僧的經文進入尾聲。
“
「我跟她有點像,但不代表我就是她。」小A默默地穿起內褲這樣說,手裡搜索著我的球衣。
「其實我是知道的,妳喜歡的是宇對吧。」一直都是知道的,我們不會有結果,即使釋出多少的善意結果都不會改變。
老實說我已經看過了他們之間的訊息對話,他給我看的。
「所以我跟妳告白的話妳就會跟我在一起嗎?」宇。
「或許吧?」A。
「什麼叫或許?」宇。
「就是我也不清楚,我可能要跟小TA獨自相處過後確認了才能告訴你。」A。
「沒問題,我等妳。」小宇一字不漏的把對話擷取給我,並且留下一句話讓我思考許久。
「我喜歡宇,但我更喜歡你,小Ta。所以我才會和你進房間,任由你為所欲為。」小A轉過身背過我繼續說著。「我知道你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一個人。」
「我....」剛想解釋什麼,小A忽然再次轉過身來面對我,眼裡盡是淚水。
「但我不怪你。」”
二跪拜,下過雨的路沾惹一襲泥濘,醒來的人拍了拍土表示嫌棄。
“
「廷勳,其實你那個時候對她說,你對好人很心軟,註定是個會失敗的人,不知道你還記得嗎?」
反覆看了看通訊文件裡塵封的、散落的文字,想試圖按圖索驥尋找出還有可能的理由。
而時間的涓湧並未稀釋了什麼,只能找一個別人看起來不太傷害自己的方式安放著;再石子丟入問題核心前慌張的遮起漣漪。
「我記得。」通訊文件裡的我回答著,而在手機前我已經開始記不清了。
文字勾勒出遺忘的前奏,由破碎的咖啡杯及過於急躁的心跳搭襯在後方做個背景音樂。
「我只想說,我會喜歡你的失敗的。」當時的小沐躲在學校宿舍蓋著棉被偷偷地打這段話。
回憶的那個樣子還是很美,讓人捨不得去練習捨得;回到那個燈紅酒綠的街,越來越急促的步伐。
一個值得被愛的人,身上會散發著某種光芒,那不一定是最耀眼的,但肯定是被需要的。
而分開的過程就像是那個人不再需要你的光,從而摸黑走向另一道光的開始。
謝謝妳,讓我曾經感受過被需要。
「我會喜歡你整個人的。」隔天小沐的眼睛是紅的,不知道是因為熬了夜還是什麼。”
三跪拜,頭頂著地的我忘記了該怎麼站起來,說好的不流淚但還是沒法忍住。
「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玉米微微笑的點了點我的頭,腳底下驚奇的泛起蓮花,引領的孩童頑皮的捏著她的手,像極了當時我們還在兒童營隊時手牽著手玩團康。
「晚安了,我夜裡的太陽。」抬起頭,以單膝著地的方式緩慢地撐起身子。此時唱誦已然結束,大眾或站或坐的等著前方老僧的開示。
「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
而面前擺著玉米的照片似乎來不及拍個符合年紀的,罕見的放了張高中畢業時拍的那張,還是由我提供的,笑容燦爛。
供桌前的鮮花水果,禮奏配樂都不及老僧開頭的一聲唵。
我聽著舊播音器靜靜閉上眼睛,拼湊和玉米的點點滴滴;支離破碎的出現在我人生中,卻在歸為塵土時感受完整。
一篇撰著因無知而遺憾的人生,都有個人幫忙惦記著;以至於不用乘載過重,導致灰飛煙滅。
沒經歷過失去,何以擁抱珍惜。
「我喜歡你寫結局的方式,看完以後好像那些難以釋懷的悲傷都真的能好好地放下。」玉米聽完地下live的演唱會時這樣對我說,我再送完公主後搭車後折返。
這句話的重點在,“好像”。
「妳看我多幸運,寫的歌有很棒的夥伴和我一齊完成、追夢,寫的故事有妳默默的看完也偷偷地流淚;我再走完這土地時早就放下許多事情了。」說出這句話的當時正處於劇本比較平穩的時候,也不知道熟悉的崩塌會在不久後降臨,不意外的又是玉米救了我。
let’ see where we wake up tomorrow..
第三段幕簾逐漸闔起,慢慢地褪去穿戴已久的戲服,也順便撕去貼在腳踝上的標籤。
生命就是一個來來往往的劇本,有人來了,鑲上回憶;有人走了,留下祝福。
而我們能做的就是感恩,不再緬懷過去,用自己的步伐慢慢的走向未來。
此時我向殯葬樂隊借了把吉他,搭載著老舊播音器裡的六字大明咒撥了撥吉他弦。
「答應妳,我會好好的。」
相片裡的玉米笑著,所以我也笑了。
我會好好的 故事未竟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